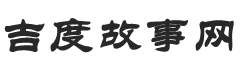我和伍长发,还有你们四个(委)员分别包一个班,先做通各班班长工作。你看咋样?
他扭脸看王校长,王校长站起来,点点头,把双手抄在袖筒里:
那中,那就这吧!散会!老师们留下来,同学们回去分头开始工作!
此后的一个多月里,农中更像农中了,上午砍树,搬石,和泥,补墙,换椽子。下午上三节课。学生娃们干,老师们自然也没闲着。老瓦从房坡上卸下来,多数不能用,挑挑拣拣,凑合着苫了三间房子。剩下的没了瓦,王校长发动大家到山上割黄白草,一律苫成草房。人多力量大,一二十间破房子转眼焕然一新,老师和几位职工的家属先后搬来入住。老师们就此不再和我们在一个食堂排队,都在新家门口,砌了锅灶,各自开伙。
那天夜里,我和李大川起来解手,从茅厕里回来,隐隐约约看见几个人影往后院跑,正要去追,李大川拦住我,挤眉弄眼地说:
别去!他们去后院听墙根儿哩!
听啥墙根儿?又不是有人结婚?!
见我不信,他扯着我的胳膊:
走,我领你去看!
进了藏经楼后院,我一看,好家伙,除了程老师寝室窗外没人,几乎每个窗口都趴着一两个黑影,有的能看出来是和我一个班的,有的是外班的。见我要大声呵斥,李大川捂住我的嘴,抬了抬腿:
可别喊!
他拽住我悄悄走到他们身后,抬脚朝每个撅着的屁股猛踢一脚。他们一扭脸,看是我,爬起来就跑。屋里立马没了动静,只有最西头的一间屋响起了咳嗽声。听声音,像是王校长。我和李大川也不敢停,退回前院。第二天,王校长让欧阳副校长给学生会干部和各班班长开会,再次强调纪律,一旦晚上发现熄灯后还有人乱蹿,坚决严肃处理。听墙根的事儿就此刹住。还有一样变化就是,后院另外盖了两间茅厕,方便老师们方便。后院和藏经楼之间的小门也不再敞开着,一到晚上十点以后就落锁。
回到寝室,我悄悄问李大川:
咋没人听程老师的?
你晕啊你?程老师老婆没来,你不知道?
为啥没来?
那我会知道?我去茅厕尿尿的时候,听见一个老师说,程老师老婆要和他离婚哩!
那为啥?
李大川伸出右手比划了一下:
装!右派啊,帽子还戴着哩!
平日里看着李大川傻乎乎的,信息还怪灵,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我说:
扯淡,睡觉!
李大川的话很快得到了验证。一连几天,程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一板正经,不再像往常谈笑风生。校园里见了,他也不再主动和我说话,好像也忘了告诉我高考作文题目的事儿。我想问,也不敢开口。直到那天下午上课钟敲响,程老师夹着课本,托着粉笔盒进了教室,班长喊了“起立”,“坐下”,程老师终于爆发了。他把课本摔在课桌上,拍得“啪啪”响,粉笔灰乱飞:
我喝酒了,我喝的是我自己的酒!
我和同学们抬头细看,程老师果然脸红脖子粗,双眼迷离:
我喝醉了,下午的课,你们自习吧!
大家目瞪口呆,一时无人说话。李大川嘴贱,双手敲打课桌像敲鼓:
老师喝酒了,大家自由了!
还未跨出门的程老师猛然站住,身子乱晃:
我叫你自习,你耳朵塞猪毛了?
老师你骂人!
妈那个X!我骂你咋了?你要是我娃子,我还不揍扁你个鳖娃儿!
忽然听见平常文质彬彬的老师说粗话,不知道是谁先“哈哈”笑了一声,紧接着,像传染似的,几乎所有的同学在吃惊之余,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现在仍想不起来,我到底笑了没,就记得程老师的红脸一阵白,一阵青,厉声喊我的名字:
伍长发!你笑啥笑?
我,我……
(委)屈,耻辱,悔恨,一时涌上心头,我竟然口吃了半天。
你给我查查,都是谁笑了,一会儿把名单报给我!
我又不是班长,就是查,你也得叫班长统计啊。见程老师暴跳如雷,我哪里还敢犟嘴,只能低声地回答:
对不起,我查!
你见过老师喝醉后的样子吗?分享一下,尽情留言。
Copyright @ 2021吉度热线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.